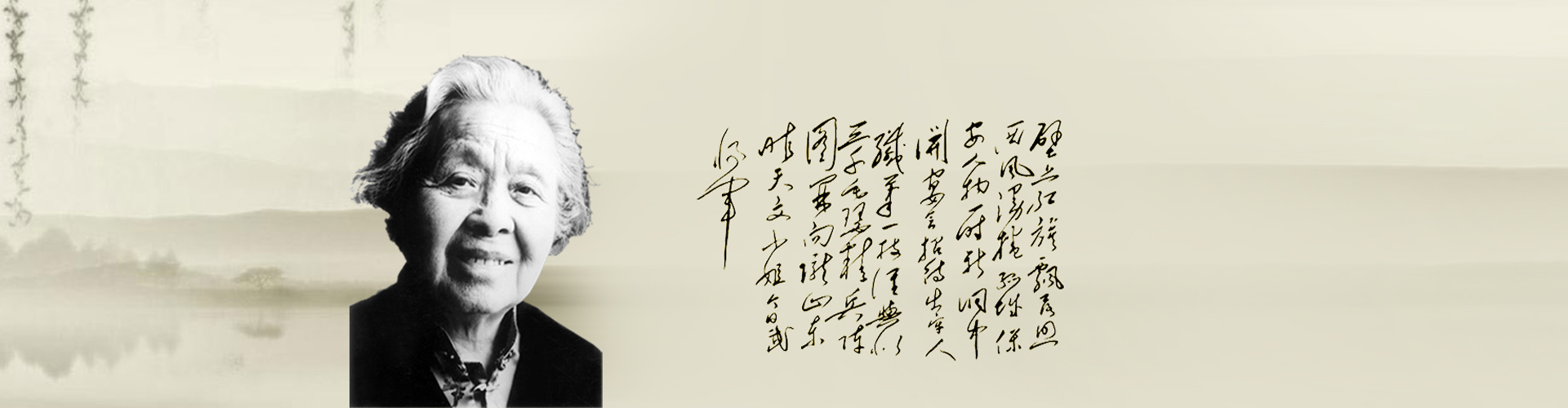2021年第4期 

桂树无香 □颜沛然
[返回]桂树无香
□颜沛然
娄源并没什么变化,似乎我从来都没有离开过。县城里随处可见的八月桂,树冠恣意地扩张,这棵要抢那棵的地盘,那棵除了捍卫地抵挡,另一头也不忘伸出到并非本分的范围。曾经,县城投集团在一项绿化改造工程中,大手笔采购成型的八月桂,替换原来的梧桐、女贞等树种。没几年,八月桂身价巨跌,曾经上万元一棵的只值七八百元,十分之一都不到。那批桂树不知什么原因,一直都不肯开花,管理者便连树冠都懒得修剪,一城的八月桂,便听天由命地生长。它们落户城区时,我已远遁他乡,从某个角度来说,正是它们逼着我离开了生长于斯的娄源。
城东郊的山包上,也栽有一片八月桂,和城区的桂树同龄。听人说那些也是公树,也从未开过花。桂树林中,找到一处坟冢,冢里的人享年四十一岁,占据着我离开娄源之前的大部分记忆,曾经,他酷爱桂树。娄源的花苑小区,有一棵硕大的桂树,其冠之下能摆四五桌酒席,我和冢中的人,在堪称娄源之最的桂树下,喝过数不清场次的酒,最惯常的情景,是应着一片熟悉的树叶轻悠飘落,同时一声低喝:“干!”
秋风掠起一林子的桂树缓缓摇曳,有叶片轻轻飘落,瞬间湿润眼睛。往事它还在吗?它肯甘心,跟着一阵秋风离去吗?
我的父辈和曾卓的父辈,在娄源城区东郊的河口村相邻而居,打小,我和同年的曾卓一起嬉耍,共同成长,被村里冠名为油盐坛子。谁油谁盐,不需分明。
初三下期,阴历二月的一个周末,一伙人在同村兼同学的李涵日家里鬼混。李涵日的父母外出旅游,他独自在家,一段日子以来,我们在他家里吃喝拉撒加胡闹,放肆得就差去捅玉皇老子的天花板。晚上,我和曾卓窜到李涵日家屋后,袤延的土地中间,有一处低矮的小山包,覆盖着杂树与灌木丛,更远处,山峦连绵起伏。夜色深沉,柔软的春风穿越山包上的小树林,朝着一大片土畦吹拂。
我俩摸着黑,在一畦菜地里,拧两兜白菜,扯一把葱蒜,回到李涵日家。李涵日双手一摊:“搞不成,肉和油,都扫光了!”“去卓哈家拿块腊肉!”我建议。“行!”曾卓毫不犹豫,一锤定音。“哈宝”是娄源县城关系较好的人之间显得亲昵的一种称呼,同憨宝,蠢得可爱的意思。我们惜字如金,省略了宝,觉得那更加亲密,叫曾卓为“卓哈”,叫李涵日为“日哈”,我被称为“骁哈”。
腊肉在二楼,从独立楼梯间上去,曾卓有钥匙,探囊取物一般轻巧。他非要我陪同,我没有拒绝,就像我有时非要拉上他,他也不说二话。不知那是依赖还是默契,或是绝对信任,总之我和他但凡有事,不必管谁的主张,只要一个开口,另一个肯定慷慨以随。
曾卓的父母在一楼的厅里看电视,我和曾卓轻轻地开了楼梯间的锁,他进到房间,我负责把风。远远地传过来咳嗽声,好像有人朝地坪里走近,我轻声地告诉曾卓,如果还没弄好,就放弃。曾卓没应声,黑暗中看到他,从楼顶梁下取了一块肉,放入夹克的衣兜,夹在腋下。连门都没有锁,仓皇狂奔,跑回李涵日家。哧溜一拉,扯开夹克,亮出腊肉。
腊肉的上部爬满白晃晃的肥蛆,夹克及衬衣上也有蛆,正一拱一拱地挪动。我清楚地瞥到曾卓打了一个颤,却没有扔掉腊肉,一个颤之后,他镇定地说:“生过蛆的腊肉特别香,有人就偏爱那味道,蛆是高蛋白,肉蛆不比粪蛆,很干净!”我们没心思听高级理论,止不住地呕。此后,我经常清晰地回忆起那块肥蛆拱动的腊肉,一掠过画面,心头必定翻江倒海。
我们还是干掉了那块腊肉,曾卓说得没错,当晚的白菜梗儿炒腊肉,确实格外地香甜,不知是否饿昏了的缘故。大快朵颐之后,已是深夜十一点,无聊少年,决定去屋后玩节目。
如幽灵似鬼魅,穿过土畦进入小树林,一队四人一队三人展开对抗,不用说,曾卓和我同一个战队。玩的军事对抗游戏,应该是后来的CS的雏形,武器是真正的“手”枪,竖起拇指伸直食指,其余三个手指勾起来,一把枪即装配完毕,枪声由嘴发出,“biu”一声,威力极大,子弹用之不尽。
我和曾卓及另一队友兵分三路,途经树林里横七竖八的坟墓,向敌方匍行进攻。当我和另一队友跋涉几百米,全歼敌军并胜利会师,发现曾卓没有来。折过去两百来米,接近山包,曾卓响应了我们的呼叫。
他掉进一个深坑,一直呼叫,起先隔得太远,我们无法听到。长方形的深坑边新土堆垒,还带着水湿,很显然是一个刚挖好的坟坑。被拉上来的曾卓,跌下去时崴了右脚。他一颠一踮,像一个小儿麻痹症患者,嘴里骂骂咧咧,说要把坑填平。
我们大吃一惊,别说工程量大,填人坟坑,那太没名堂了!坟坑是阴间的地盘,阎王爷会不会不高兴?李涵日等几个,坚决不同意,曾卓咬着牙对我说:“你帮我!”我点点头,应下一桩灭天理的勾当。李涵日几个走后,我俩梭溜一圈,在土堆外找到了锹铲、锄头、箢箕,曾卓拖着不灵活的右脚,和我折腾两个多小时,终于把别人可能花了一整天甚至几天才掘出来的土,重又回归原处,曾卓恨意未消地用铲子把面上的土拍打了十多分钟,直到那儿平平整整。
逝者家属,另择了坟地。村里人从此叫我和曾卓天杀的报应,我俩在河口村,史无前人。
进入高中,天杀的肆无忌惮,更上层楼。高中生曾卓,走路昂首阔步虎虎生风,散发出大马金刀的威然。午间休息时,我和他一起去操场,途中一处花坛的水泥边沿上,蹲着一个青年,冷冷地横瞪,似是非常厌恶曾卓的气势。“瞪什么!”曾卓感受到挑衅的目光。“瞪你怎的?小崽!”那人双眼一鼓。曾卓冲过去,那人猝不及防,被推进花坛里,我紧跟着曾卓一起跳入花坛,狂踢猛跺,踩踏一轮。下午放学后,我和曾卓一前一后走出校门,五六个青年朝我们包抄过来,手上都拿着刀子。那个被踩进花坛里的家伙冲过来,刀子正正对准我的额头,我脑袋一偏,刀子砍在左手臂上。我经常跟人打架,也挨过别人的拳脚,却第一次中刀子。手并不疼痛,好像没连在神经上,意识一片空荡。不过清楚地看到,身后的曾卓一步跨到我身前,右手一抡,迎住了再次砍向我头顶的刀子。曾卓的左手,拉了我一把,我和他一人掩着一只血淋淋的手臂,发足狂奔。砍我们的人,是娄源城区的混混,还是一伙人的老大。他到我们学校散心,没想到被两个笨头笨脑的学生蹂躏一番。我和曾卓的手臂各缝了二十多针,惨痛的经历让我们真正见识了江湖,江湖,不是拳来脚往,炫耀一下威武,它是真真实实的刀光剑影加血腥可怖。我不敢猜忖,如果没有曾卓的一挡,那一刀是否会将我的脑袋一劈两半。我在心底里默认,曾卓救过我一命。那一刀一直在我的生活中心有余悸,每想起那一刀,我都会暗暗警告自己,小心做人,收敛勿妄。
我和曾卓沿着江湖的边缘进入社会,跟人拉过帮结过派,对人舞过刀子,但从未正儿八经砍过人,所以没跟那个栽进花坛的人一样,被政府绳之以法。江湖虽野,却能锻炼人,娄源一些财大气粗的老板,其中多数在江湖中闯荡过,甚至还有在刀口上舔血的凶狠之徒及刑释人员。我和曾卓,也算被江湖淬炼过,有一天,忽然明白,不能做一辈子报应,得做个好人。
我俩翻身上岸,朝创业的道路奔去。我有一个表哥,在政府部门工作,介绍我到一个做工程的老板那儿打工,有一份相当不错的待遇,不过跟曾卓比,完全不值一提。
曾卓的表哥张顺,在北方做煤生意,吞吐量非常大,单笔业务动辄几百万。曾卓给张顺打过几个月下手之后,找亲戚朋友凑出一笔钱,开始做放息的生意,说透一点,就是高利贷,在娄源县,萝卜白菜一样平常,放息的人,称为高先生。曾卓不似一般的高先生,他的款只放给张顺一个人。曾卓的生意很顺当,打工的我,在经济上很快和他没有任何可比性。我俩仍然经常聚首,仍然油不离盐,不过别人不说,他不说,谁油谁盐,我在心中,暗暗地划了等级。我有时候会生出自卑,但没有一丁点不高兴。他和我是发小,共过生死,有最珍贵的友情,跟金钱不带任何关系,谋生来说,他有他的道我有我的桥,他混得好赚得多,我真心欣慰,我赚得少,但能过日子,也很安然。
很快混到二十多岁,恰好李涵日的表妹梅映雪从偏远的小镇来到娄源县城。十九岁的梅映雪,除了长相与身材,其他方面有点辜负带着诗意的姓名,文化程度初中,性格泼辣张扬,还爱喝酒,比女汉子更过去几里地。我曾想象过,真有一场雪在她眼前,她才没兴趣把名字贴近现实相映成景,她可能会扛个大大的竹扫把一顿乱涂,但那确乎是她的名字,而我也没觉得那有何不妥,如果真扛个扫把去涂雪,我并不介意陪她一起去。
梅映雪在李涵日的伯父的茶叶店做事,工作很轻松,闲暇间常跟着我们混,她少女老成,为人灵泛,说话直爽,处事索利,拿得起放得下,江湖女侠的范儿,让我们生出亲切的喜欢。我和曾卓还没有女朋友,都想接近梅映雪。
那晚,一帮人在百乐门饭店喝酒。半斤装的小糊涂仙,五十二度,上了十几瓶。一伙人兴致挺高,多的干了一瓶以上,少的也有三两多,唯独我表现欠缺,没喝多少。梅映雪见我没跟上,提一瓶酒走过来,将瓶子杵在我的酒杯旁边,再站到椅子后,箍住我的脖子:“骁哥,吹完这瓶,我就做你的女朋友!”
李涵日说:“那怎么行,你表哥还没表态呢!”梅映雪一条腿斜刺踢向隔一个座位的李涵日:“关你屁事,本姑娘乐意!”
她脚下不稳,箍住我的双手往后拖,差点把我连人带椅掀翻。幸而她很快收回踢李涵日的腿,重又站稳,我才没有仰面倒下。
“骁哈,放开那瓶酒,让我来!”“映雪,选错了,骁哈不行,你选我,我吹两瓶!”桌上的人起哄。
“都不要,就选骁哥!”梅映雪双手又使劲一箍,我陷入呼吸困难,差点就要握住那瓶酒,准备一饮而尽。猛然间,看到曾卓没响应,还冷冷地盯住我。那是对我从没有过的眼神,我心头一凛,瞬间心知肚明。
“映雪,别闹!今晚确实不胜酒力,下回再补上好吗?”“没闹!不是酒力的问题,要不,我吹掉这一瓶,你做我的男朋友,行吗?”
再瞥一眼曾卓,他已收敛凌厉的目光,表情特别平静,让人看不出是什么态度。但我明白,非常明白。
“还说不是酒的事,感情怎能用酒来度量?那肯定不是真爱!”我极力按下心头的冲动。
“酒就是真爱!喝不喝,你不喝,我喝!”梅映雪松开我的脖子,伸手向桌去拿那瓶酒。
“我不喝,你也不准喝!如果喝趴一个,怎么真爱!映雪,还是把真爱留下,以后慢慢地滋润我们!”我拦住她的手。
“真没劲,讨厌你!”梅映雪瞪我一眼,转身走回自己的座位。
“来,一起喝一个!”曾卓向在座的人举起手中的杯子。我一杯一杯闷闷地喝,终究搞定了那瓶酒。梅映雪回座之后的细节,我都没留意,也不想在乎。但记得曾卓放肆痛饮,某杯酒之后,豪气地说,他曾为我挡过刀。我一直很清醒,清醒地听懂了他话里的意思。
十点多,一伙人从百乐门出到马路边,瞧着醉意熏熏的同伴,我无限纳闷,明明喝过了平时没达到的量,我反而醉意全无,异常清醒,我应该那样清醒吗?
曾卓站到路边拦的士,接连过了好几辆,都没有停。干脆站到路中间,一辆黑色越野车发出刺耳的刹车声,趔趄着停在他面前。他一巴掌拍在引擎盖上,吼一声,“租车!”车上下来一个年轻人,见我们有一伙,收敛起发作的情绪,回到驾驶位上拨打电话。我想拉开曾卓,他不理会,继续拍打引擎盖。围观的人,一波一波,挤在路边看热闹。后面又来了车,喇叭声凌乱尖锐,此起彼伏。
曾卓从身上掏出一沓钞票,在引擎盖上啪啪地敲,“租你的车,算卵呢!”我劝,李涵日也劝,曾卓不听,继续拍打。十分钟后,年轻人下了车。我看到几十米外,黑压压一伙人正急急走过来。
“给这么多钱,还不租,怕是个蠢包!”站在路边的梅映雪,突然走到车旁,朝着翼子板踢了几脚。
“你个疯婆子!”年轻人突然对着梅映雪怒骂,像是一直忍着却终究没忍住。
“算卵呢!什么玩意!”曾卓大吼一声,臂一举手一扬,明亮的路灯下,飞舞起一片火红。看热闹的人一拥而上,越野车前头群蜂涌动,乱乱哄哄采集着飘扬以及落下的钞票。
年轻人走到梅映雪面前,扬起左手。曾卓一个箭步过去,右手一举掐住年轻人扬起的手,再反手一拧扣住手掌,使劲一按,年轻人不由自主地矮下身子。“小崽,敢动老子的女人!”曾卓睁圆酒意催红的双眼,仿佛要喷出一座火山来。
远处那伙人已经近前,刀闪棍挥,我暗暗叫苦。“骁哥,怎么是你们!”竟有人跟我打招呼,仔细一瞧,惊魂安定,来的那一伙,领头的人是我和曾卓混江湖时曾照顾过的一个小兄弟。一伙人不打不相识,干戈化玉帛,寒暄过后,我忽然发现,曾卓和梅映雪不见了。
那晚,随一阵六千多元的钞票雨飘落的,还有我的一段莫可名状的惆怅。
没多久,曾卓新婚大喜。我在怅然若失中度过一年,也成了家。我和曾卓各顾各灶,终于,油是油,盐是盐。此后仍经常见面,他更加风生水起豪意勃发,所交道的人五花八门,还结识了县政府的大领导。嫁为人妇的梅映雪,一改做女孩时的强势与张扬,在丈夫面前温恭谦礼服服帖帖,一点都不显得稚嫩,令我不禁生出恍惚的感慨,女人真的很难让人看懂。是曾卓有非凡的驾驭能力,还是梅映雪本就是表面张扬实则内敛的女人呢?莫非她年纪轻轻就修炼得大巧若拙了?那个时候,我还清楚地记起李涵日的伯父对梅映雪的一番评价,那妹子聪明灵慧又极有主见,可惜的是少读了一点点书。我试着把李涵日伯父的评价与我的关于梅映雪的猜忖有机结合起来,却觉得那跟她为何服帖于曾卓没有多大的关系,事实上,得出答案也跟我没有丝毫关系,我放下莫名其妙的想法,一心一意专注于自己的生活。
曾卓夫妇宴请新朋旧友,我家也在被邀之列。宴前给宾客包括小孩都发了一包“和天下”香烟,但没有给我和我妻子。席中酒意酣然,曾卓再次豪气勃发,说要双双发达,又每人一包,还是包括小孩,还是和天下,还是忘了我家。席散,妻子怏怏不乐,我心中也郁闷,如果是旧友不发,李涵日夫妇却有。我只能跟妻子解释,以我跟他的交情,一家人一样,哪还用得着讲客气。其实心中的另一种想法是,我与曾卓已经差着档次,他可能渐渐地瞧不起我。妻子心眼小,一直耿耿于怀,我心眼也不大,偶尔会想,为什么没发烟给我家。再一两年中,少有见面。
娄源县城实在太小,我住进花苑小区,才知道一月之前,曾卓家也住进了那里,他二栋,我三栋。我们重又做回油盐坛子,但油与盐已经相当区别,我是十五年的按揭,房奴的身份,他是全款,真正的业主。无意中又做了邻居,是天意修缘,妻子也不好意思再计较,与梅映雪相处很好。两家经常一起聚餐,要么我请客,要么他做东,天气好的话,还会在小区的大桂树下,开怀畅饮。
曾卓的生意只有一块业务,收聚别人的资金再放给张顺,赚利息差价,当中有一部分是几个政府领导的投资,曾卓一分钱差价也不收取,全额付给那些领导。放到张顺手上的钱,滚雪球一般从二百万到逾千万,逐渐就接近两千万,有一段时间里,曾卓的利息抽成,一个月就有三十万。我是个蠢宝,没领悟到曾卓的投资暗示。那时候,除了打工,还在老板手上承包一些小项目,看似利润高,其实不然,要垫资,要理顺各路关系,一通下来七打八扣九剃毛,到手上能有一成以上的纯利,算是很不错,张顺做什么高级生意,能付给借款人三至四分的高额月息,生意真顺手,为什么又老是要借钱呢?我吃自己的饭操别人的心,总担忧张顺不靠谱。有那么几次,小心翼翼地跟曾卓讨论,他不是摇头笑我就是故意岔开话题,神情里特别的不屑一顾,让我忍不住惭秽,生出“无钱休入众,言轻莫劝人”的自卑。
住进花苑之后,通过曾卓认识了魏慧。魏慧比我们大整整十岁,保养得不错,长相也还可以,要仔细观察,才能从她脸部的粉底之下,分析出她有着比我年长十岁的痕迹。魏慧家庭条件很好,老公在深圳开厂,她在娄源留守,每日里悠闲自在。我和曾卓家的聚餐,她会经常参与。她还有一个身份,是曾卓女儿的干妈。我很快发现,曾卓与魏慧之间的关系,直接地不正常。曾卓倒也不瞒,有一回要我为他驾车去省城,途中魏慧上了车。在省城的平和堂,魏慧看中一个一万八千元的包和一件九千多的外套,曾卓爽快地买单。晚上的住宿,只开了两间房,我特殊享受,独住一间。
我问曾卓,你同魏慧的关系,映雪知道吗?曾卓答,知道。我说,你这样她能忍吗?他说,又没有抛弃她。
我确实是蠢宝,某回喝了一点酒,居然去问梅映雪。梅映雪瞅我一眼,平静地开口,别听人胡说,魏慧是曾卓的合作伙伴!
我又跟李涵日说,他嘿嘿一笑,公开的秘密,全世界除了魏慧的男人,哪个都知道!
我说,讲不通!映雪虽然读书少,但人很明白,怎么就容忍得下?
李涵日说,女人的心思,谁弄得懂!
曾卓也常带梅映雪去省城购物,我和我妻子,做过几次陪客。去的商场,几乎每次都是平和堂。曾卓一分钱价都不还,即购下一件三万多的皮衣,这让在同一家店里为一件三千元的外套磨破嘴皮讨价还价的我,恨无地缝可钻。幸而梅映雪不是追求奢华的女人,她选购的衣服,相对普通且不昂贵,才使得我妻子不那么尴尬而我也不至于更加羞愧。
借到那笔钱之后,决定从此不再陪曾卓去购物,我也有自尊,无法承受一次又一次的沉重的失落。借钱时,曾卓当场指示,魏慧转账五十万元给我,我打借条给梅映雪,载明月息三分,签名并具手膜。
李涵日跟我说:“没想到,骁哈跟卓哈借钱,也要算利息。”我说:“做的这行生意,算息天经地义,而且魏慧要四分的息,看曾卓的面子,才算了三分!”“就你骁哈,是秤砣做的心!”李涵日嗤之以鼻。
我的老板改行做房地产开发,我在他手上,带资垫款承包了上千万的工程,向曾卓借钱,是下下之举。此前已经借遍亲朋好友的钱,达七百万之多,有要息的也有不要息的,利息最高一分五,是我认可的范围。整个工程的投入,还差一笔资金,再无办法,只好跟曾卓开口,他要三分的息,我认,比起工程完成,本金和利润一并结回,那五十万的三分之息,算不了什么。
老板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之下跳楼身亡,晴天霹雳跟着我,从早至晚轰隆炸响,持续一个多星期。我给债主逐一寄信,词恳意切地说明,无法再算利息,但本金,只要留得命在,倾家荡产做牛做马都会想办法归还。
曾卓那头我没有写信,直接摊牌。他先摇头,再苦笑,“钱是魏慧的,不算息绝不可能,如果是平时,给你垫一下,甚至帮你出了,也不是问题,但现在顺哥那边几个月没付利息过来,我也非常紧张。”
说的是实情,除本金外,张顺确实已欠了他很大数额的利息,其中一部分,他必须为张顺垫付给别的债主。介绍我去打工的表哥,那时已是娄源城投集团的负责人,他积极地为我张罗一些项目。那些项目让我得以苟延残喘。年底,有人用刀子比着我要债,我都没理会,我挤掉一切开销,只偿还了曾卓的借款,连本带息七十五万,一天的利息都没有少算。他没跟我客气,非常真诚地说,谢谢兄弟的理解。
除夕,我与妻子躲到偏僻的乡下,过了一个极不平常的年。来年开春,曾卓的危机全部显露出来,张顺承诺的节后付息再次落空。债主们上门索要,还有的开始追讨本金。曾卓跟魏慧挪了一百万,梅映雪也从娘家借过来一百多万。但是只够开销一小部分。
我继续在城投集团做项目,表哥告诉我,县城要搞城市绿化的提质改造,项目不小,有两千多万的工程量,不出意外的话,能争取到。我满怀憧憬。
张顺一直没还钱,曾卓继续硬撑,拆东补西,垫付经手款项的利息。梅映雪单独找过我,说曾卓认死理,不去逼张顺,又不跟其他人暂停付息,那样下去,岌岌可危。
约曾卓到桂花树下喝酒,我看到他原本俊朗照人的脸,被愁淡的眼神渲染,苍白中散发出一片衰老的暗色,三十几的年纪,头顶竟窜出此起彼伏的白发。我也曾受过打击,并没有那般憔悴,按理说,曾卓气魄比我大,做事也比我坚决,应该比我更能承受压力,怎么就给人一蹶不振的感觉呢?
都没有说话,默默地举杯默默地喝酒。我的脸颊开始发热,曾卓的眼窝周边,也泛出一片深红。
“时代变迁,规则更改,最近,国家对民间借贷重手整治。卓哈,曾经你因此而风生水起,但如今世道异变,也该改一改思路,不能只吊死在一棵树上。未入黄河先寻败路,还没到不可收拾,赶紧调整及时止损。我不敢说自己能够做你的例子,但我有信心,留得青山在,哪怕天天担柴卖,也可以一步一步东山再起。”
“我相信顺哥,他暂时遭遇困难,我必须全力以赴。一定会好转,万一败了,我认命,来,喝!”酒意燃烧低落的情绪慢慢高涨,曾卓坚定地说。
我有自知之明,自从我给别人打工之后,曾卓就再没有听取过我的意见。酒确实可以忘愁,我的脸颊越来越热乎,他的眼窝越来越深红。我们来了兴致,回忆起年少的轻狂,回忆起江湖岁月的混沌。他曾为我挡过刀的话题必不可少,说起时,我心头一热,如果没有那一挡,可能世界上早就没有了我!那一挡,胜过我和他之间的任何一件事!
那回是我同曾卓最后一次喝酒,直到凌晨两点。我没有说服他,甚至根本谈不上劝。桂树下,柔绵的风轻飘飘地抚摸热烫的脸颊,两者中和一起,我的身体里奇异地清清爽爽,仿佛经受了醍醐灌顶的洗礼。尽管,不知道接下来的岁月,等待我的是什么。
没过几天,有一个晚上,我辗转反侧。“我为你挡过刀呢!”这话猛然窜出来,窜得我更无睡意。十二点半,我敲开曾卓家的门。
“你有周副市长,他抓城建,我有表哥,这个项目,一起合作,绝对搞得定!”我兴奋地说。“这么大的项目,仅凭他们两个,不可能做得下主!”曾卓没有激动,直摇头。“你不愿意参与?”“少吃咸鱼少口干!顺哥那边,正准备拿土地抵押贷款,需要配合,我没有那么大的精力,你自己好好把握吧!”
半个月后,表哥找到我,“昨晚上,曾卓来找我,出手就是四十万现金,我说,你跟骁哈不是生死弟兄吗?他说,骁哈不搞呢!”
我一阵惶然加凄然,不搞?我还指望这个项目逆转人生。“放心,周副市长,还不足以压住我!”表哥说。然而好运没有眷顾我,更关键的大领导出面干涉,表哥完全没有抗拒的资格。
我心如死灰,把儿子托付给岳父母,和妻子南下深圳。背井离乡的日子里,先在建筑工地上混,后来开拖拉机送泔水、送粪肥,我和妻子省吃俭用,一分一厘地还债主们的钱。天无绝人之路,请我开拖拉机的农场主人在城区开了好几个酒楼,他将其中两处承包给我。几年下来,我终于敢堂堂正正回到娄源。
被迫远走他乡,我只跟李涵日联系。离开娄源之后的一些事情,我从他口中得以知道。
那年,曾卓拿到了绿化改造工程,赚下七百多万,还掉一部分债务,又凑出四百万借给张顺。李涵日、魏慧、梅映雪都劝他,张顺的妻子、儿女,早就移民国外,那是做翻不了身的准备。张顺的亲姐姐也说,曾卓你不要再投钱,张顺的坑,如来佛祖都填不起。
曾卓告诉李涵日,张顺有土地在手,只要从银行抵押到贷款,绝对可以满盘复活,投在张顺那里的钱,连本带息已逾两千万,救张顺就是救自己,张顺活,他不会死,张顺死,他也活不了。
没多久,张顺因诈骗罪入狱,判了十五年。曾卓彻底死心,变卖家产偿还债务,除开利息,仍欠下别人的本金一千一百万,其中有三百万,属于梅映雪娘家的兄弟姐妹及各房亲戚。
“欠了魏慧多少?”我问李涵日。“卓哈说有两百多万,映雪说一毛都不欠,魏慧也说没欠!”“到底有没有?”“不可能没有!”李涵日坚定地回答。
房子没了,车子没了,日子还在,梅映雪安慰曾卓,“我家那边的钱我去打招呼,其余的,你恳求人家宽限日期,我们重新开始,一步一个脚印来,实在转不过,学骁哥去打工,慢慢还人家的钱!”
梅映雪开了一家餐馆,后来又开了一家水果店,那一年,她还有了身孕。曾卓不想再要孩子,娘家人也劝梅映雪拿掉。她都没听,说要借孩子给家里冲扫晦气。孩子出生,是个男孩,算得上是喜气。
一开始,曾卓老老实实,指东到东指西到西,一切对梅映雪唯命是从。曾卓也四处寻机会,想要翻身,但此时非彼时,他完全比不上梅映雪的心态,大事没有资格做,小事没有兴趣做,很快就心灰气馁,每日里到外头借酒浇愁,或是跟魏慧搅在一起。梅映雪到底气恼,同曾卓闹一场,“硬不想好了,散伙!还想好,我管店子赚钱还债,你管生活,带孩子!”
曾卓却很快故态重萌,梅映雪的家人都劝她离婚,她却说,自己选的果子,再苦也要咽到肠子里!
“是卓哈辜负映雪,至少他得跟魏慧断了!”听过李涵日的讲述,我说。
“卓哈也苦,以前作威作福,突然得小心翼翼地看映雪脸色,哪能那么容易转换。他跟我说,生了孩子之后,映雪经常地不可理喻,动不动发大火,有时还目露凶光,似乎要杀人,话都不敢回,生怕一不小心说错,就是地动山摇。过得憋屈,干脆烂船烂撑,在家里忍声吞气久了,就去外面放纵,在外面生出愧疚来,又回去忍声吞气!”李涵日说。
我的脑海中,很自然地浮现,梅映雪咬牙切齿的凄忿与曾卓默不作声的黯然。
“那晚和映雪赶过去,魏慧正慌乱无措,卓哈上半身斜坐,头耷在车子后窗上,下半身什么也没穿,我摸过他,身体还有一点点温度,但已经僵硬。魏慧不敢隐瞒,说卓哈在她身上,突然捂住胸部,口中连续作呕,呕过之后,头靠车窗,停顿了呼吸。”
“我要报案,被映雪制止。她说,怨不得别人,早在两个月前,犯心绞痛,汗都湿透了被子,催他去医院,坚决不去,是成心找死!”
“卓哈的手机,有一条发给魏慧的微信,还完债之后,我会安顿好一切,和你离开娄源,浪迹天涯周游世界。魏慧的回复,是一个OK。葬礼上,我们要将魏慧赶走,映雪说,她有资格进去。魏慧在灵前,没管没顾地痛哭,仿佛死的,是她的丈夫。我硬是别扭,吼她,别做太过了!她才离开。”
“映雪请风水先生,看中的坟地,居然是被你们填平的那处!”
我并不诧异,世事难免荒唐,然而哪一桩才会深刻影响一个人的一生呢?我突然狂不可遏地想见到梅映雪。
坐在面前的女人,脸很圆润,比之前更有神韵,看不出曾经历过人生磨砺的生活,听说她新交了一个男友。
沉默地坐着,似乎我和她,初次相识,却默契无限。“只是想见一面!”良久,我说。“也许,不止见一面的简单吧!”她答。我一阵面红耳赤,真有见她的必要吗?
“有的人只死一回,我却在梦里,死过千万回!”她接着说,突兀地泪流满面。我一怔,第一反应是,凄然的脸,竟然美得不可方物,是我从没见过的一种神态,她是梅映雪吗?
(责任编辑:章晓虹)
作者简介:颜沛然,1975年出生,高中文化,自由职业者,涟源传承助学会秘书长,此篇为其小说处女作。